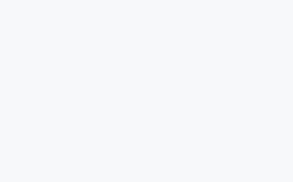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峻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茶马古道上一度辉煌的马帮运输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冒险”;人类为了生存所激发出的勇气、努力和激动人心的精神,使我们的生活有了价值和意义。

丽江结识“马锅头”
1989年,我独自一人或步行,或趴在颠簸的卡车车厢里,行程近万里,第一次领略了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唐古拉山脉,在世界屋脊上行走所包含的意义。
1990年,为探查茶马古道的秘密,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云南德钦雇了一支有七头骤子的小马帮,由马锅头都吉赶着骡马,踏上了数十年来就没有人全程走过的茶马古道,在大山大川里走了整整100天,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转了一圈,回来后余悸未消、兴奋未平地写了本《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的书,第一次将那条由云南和四川通往藏区的道路命名为“茶马古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丽江古城大研镇的纳西古乐会上认识了赵鹤年(字应仙)老先生。时年已80多岁高龄的赵老先生早已赋闲在家,守若古镇里那院古色古香的院宅悠哉养老。那宅院还是他祖上拎着脑袋奔波于茶马古道所攒下的血汗钱盖起的。每天晚上,老先生还去镇上的纳西洞经古乐会为四面八方慕名而至的游客演奏动听的音乐。演奏时,能言善道的主持人宣科都要首先向大家介绍赵老先生是老马锅头,是走茶马古道的“藏客”。
也走过这条要命的古道的我,就赶快认识了这位老前辈。私下里老先生向我解释他并不是马锅头,而只是一般的赶马人。从20多岁起,他就踏着他爷爷赵怡、他伯父赵育杨的脚印,十多年往来于茶马古道,最远甚至到过不丹、锡金、尼泊尔和印度卡里姆邦的噶伦堡、加尔各答。但他最为苦恼的是,没人相信他在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赶马生涯,甚至连他的儿孙们都认定他所讲述的在茶马古道上的种种经历纯属天方夜谭。
茶马古道和许许多多在古道上冒死来来往往的赶马人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成为遥远的梦幻,随着赶马人的一个个去世而尘没烟消。
要是时光倒转仅仅11年,在我还没有将自己的脚步踏上茶马古道之前,我也不会相信赵老先生和其他赶马人的故事,那里面充满着太多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际遇。
然而茶马古道的确存在过,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1950、1960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至今,在短途区域里,它仍在通行。在半个多世纪前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尤其在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曾在丽江工作过的俄国人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中深情地写道:“印度与中国之间这场迅猛发展的马帮运输是多么广阔和史无前例,但是认识它的重要性的人极少。那是独一无二非常壮观的景象。对它还缺乏完整的描述,但是它将作为人类的一个伟大冒险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此外它非常令人信服地向世界表明,即使所有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被某种原子灾难毁坏,这可怜的马,人类的老朋友,随时准备好在分散的人民和国家间又形成新的纽带。”
赵鹤年就是这场广阔而史无前例的马帮运输队伍中的一员。他20岁出头就到德钦,在著名的李达三开设的“达记”商号做生意,后来更长期往来于丽江、西藏、印度之间,亲自经历了茶马古道上无数的风霜雨雪和困苦艰辛。像有他这样经历的“藏客”老人已经寥寥无几。
现在,这条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艰险,也最为壮丽的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浓厚兴趣。然而,滇藏、川藏公路早已取代了过去蜿蜒伸展在大山、河谷及连接起一座座村寨的茶马古道,传统意义上带着帐篷,锣锅和枪支,响着铜铃唱着赶马调浪迹天涯的马帮也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一些日益剥蚀褪色的记忆留存在一些日益稀少的老赶马人的脑海里。“现在连过去那种用纯铜做的铜铃都没有了!”赵老先生感慨万千地说。

千年古道隐苍茫
1992年初,我来到作为普洱茶六大茶山重要集散地并作过勐腊县(镇越县)府的易武乡,从乡长任上退下但仍在主持地方志编撰的张毅先生,给我讲述了他少年时亲眼所见并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由于滇西抗战和东南亚战事的影响,茶马古道被长期阻断,藏族地区严重缺茶,战争才一结束,来自中甸、德钦的藏族马帮就蜂拥而至,一个马队就有100多匹牲口,将六大茶山的茶叶搜罗一空,甚至连多年的老茶叶也全部买走。他们付的藏银洋多得无法计数,只好堆码在桌面上一摞一摞地数个大概。闪烁的油灯下,那些沉甸甸的银洋压得桌子吱嘎作响……
易武及思茅一带的人们都把马帮来往运茶的道路称为“茶叶之路”,它由易武起始,经由曼罗、麻黑、曼撤、曼松、倚邦、小黑江(罗梭江)、勐旺、普文到思茅和普洱。许多路段都由当地有名的茶庄茶号出面出钱,当地民众出工,修桥铺石,从道光二十年始修,历时五年方才完成。它在山间密林中蜿蜒伸展,经过景东、景谷、南涧、巍山和大理下关直达远方。在茶叶上市季节,每天往来驮茶的骡马多达八九百匹。这些路至今盘旋在滇南的山峦丛林间。
其实早在唐代,茶马古道即已开通。到宋代,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及至元世祖忽必烈由西昌、丽江奔袭大理国,进一步打通了滇、川、藏间的道路,加强了各民族的联系。明、清两代,茶马互市有了空前的发展。明末,云南各族人民进行了十七年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西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达赖喇嘛立刻遣使要求恢复茶马贸易。据载,仅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6年),滇茶销西藏就达三万担!滇藏山道在那时已名正言顺地成长为一条“茶叶商道”。
至民国年间,据《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记载:“普思边沿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如何的繁忙和热闹。
抗日战争中后期,这条古道更成为中国大西南后方唯一的一条国际商道,难以计数的物资通过世界屋脊源源不断地流来淌去。
就这样,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叶的大量运输,造就了茶马古道。而古道上经济物资的大量交流,必然带来相应的其它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在这条路上,数千年的岁月积淀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它那无尽的奥秘。
而曾在这条古道上活跃过的马帮的生活,也将以其传奇色彩,以其冒险精神,以其激动人心的事迹,永远流传于世。
端午节一过,海拔2400米左右的丽江坝已经春意盎然。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的休整,在赶马人精心照料下,骡马在崎岖山路上伤损的蹄子得到了恢复,体膘也长起来了,各家商号和马锅头们再也在家待不住,他们开始张罗准备各色货物,特别是茶叶,即将再次踏上那遥远而艰难的旅途。
大多数走西藏的商号和马帮办货都在丽江。另有别的马帮,像大理的白族马帮和滇南的马帮将茶叶等西藏需要的货物运到丽江来。当然,也有大量的藏族马帮带着山货和从印度运进的外国货涌到丽江来。那时的丽江其商业之繁华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在丽江几乎就能办好一切所需的货物。
丽江纳西族走西藏草地的马帮都知道,五月端午过后上路正好,因为前去的沿途冰雪开始融化,人和骡马饮用的水有了,新草也冒出来了,他们可以一路慢慢地走去,让骤马尽情享用鲜嫩的青草,以使心爱的骠马保住体膘,这样才能够勉强支持到顺利返回丽江。当时有这样的进藏时令:“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七、八、九,正好走。”但七月出门就晚了,他们最迟必须在夏至前出发,否则他们就无法在严酷的冬天来临之前回到温馨的丽江坝。那样的话,他们甚至可能把骠马和他们自己的性命永远留在那条可怕的路上。
那一年赵鹤年还不到30岁,正是做事的年龄。他第一次走这条路时是27岁,当然,在这之前,他经常来往于丽江和德钦之间,早已习惯了在山野中行走的生活。自27岁以后,他已经在前往西藏草地的道路上走过了好几趟。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丽江人一样,赵鹤年不仅有名,还有字,叫应仙。熟悉的人就只叫他赵应仙。每次出门上路,赵应仙都要自己翻翻黄历看看,选一个黄道吉日才能出门,不是黄道吉日就暂时不动。马帮们全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信还是不信。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一旦出门在外就要不停地赶路,也就管不着什么黄道吉日不黄道吉日了。
当然,当年在出发的时候,赵应仙还要将一支十响的小手枪别在腰里,他并不知道那枪是什么牌子的,他们把那枪叫“十子”。他雇请的赶马人“马脚子”也都有枪,他们一般带的是能装五发子弹的长枪,有的是用叫“辛格伦巴”的狮牌枪,有的是用叫“明都伦巴”的花牌枪,大概都是英国生产的。这一路过去野兽很多,熊和豹子随时可见,还有贪婪而凶残的强盗,枪必带不可。那时的马帮都是全副武装。护身防卫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可以打猎改善生活,也为艰辛的旅途增添许多乐趣,而最主要的是,枪在那片广袤的高原上是男人们的标志和象征。只要是男人就要有条枪,没有枪的男人就跟阉人一样。
在漫长的路途上,赵应仙自己还有自己的乐趣。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有相当的汉文化修养,很喜欢看书,所以在他的行囊中,还有几本他最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在路上歇息的时候,赵应仙会抽空在帐篷里读上几段。在那高原荒野上伴着马铃铛的响声和松明火把读《三国演义》《西游记》,肯定别有一番特殊的趣味。他们本身的行程,就是一趟趟充满艰辛和奇遇的“西游”。那以后许多年,在赵老给我讲述他们西行的故事时,他还经常会用上一些文雅的词句,那可能就是从古书上来的。
那么长时间出门在外,要准备的东西还很多。得带上卧具和铺盖、餐具、部分主要的吃食,如腌肉、面条、糌粑之类,以及在漫长的路上需要的一切东西。帐篷和炊具什么的赶马人会带的。说起来这好像并不复杂,但真正动手准备起来,那就等于你几乎要把整套的家当都带上。那毕竟不是到什么度假村去休闲,而是要在远离文明的荒野之中度过半年的时间。
出发的时候,赵应仙已是一身藏族装束——宽袍大袖的楚巴,用一根腰带束紧,右臂袒露着。行囊里还有兽皮帽、羊皮袍和藏靴。俗话说入乡随俗,在雪域高原上,也只有藏装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也便于骑马。走西藏的“藏客”都有整套漂亮的藏装。去到西藏境内,赵应仙他们甚至要换掉从丽江穿出来的丽江当地生产的皮靴,那对于西藏的大山来说过于笨重,用布和毡子做的藏靴则十分合脚,而且暖和又轻便,连袜子都不用穿,光着脚塞到藏靴里就行。不过话说回来,他们那时也没什么袜子可穿。
跟有些地方的马帮不一样,纳西族、藏族马锅头和赶马人都没有纹身的。
每个走西藏的藏客不仅穿的是藏装,而且大多讲得一口流利而道地的藏话。赵应仙至今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藏话,一讲到西藏,一串串的藏话就迸了出来,尽管他已经50年没进过藏区,没跟藏族打过交道。赵应仙还识得一些藏文,如今还能像我们熟读汉语拼音一样,能将藏文的所有字母唱念出来,“噶咔噶哪,扎查扎哪,沙萨阿雅……”正因为有这种语言及生活习俗方面的便利,纳西族马帮才得以在藏区通行无阻,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其实,藏族与纳西族的关系,跟茶马古道一样源远流长,甚至更为深远。两个民族都属于氐羌族群,里面流着相同的血液。他们的祖先同为游牧民族,都生活在高原上。
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得丽江纳西族马帮成了这一区域里各个民族之交流的中介,使得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那片广袤的雪域草地,走向那众山之巅,走向那众水之源,走向我们这个世界的屋脊。

天各一方
像以往每次出门一样,赵应仙那病弱的妻子都要默默地送他到院子大门处,看赵应仙从门口小溪边的拴马石上解下他那匹名叫“红比”的铁青骟马,一直到马蹄的得得响声消失在小巷外,她还继续倚在大门门框上。赵应仙在走出妻子视野的时候,照例要回过头来,朝眼泪巴巴的妻子挥挥手,说:“回吧,回吧,”然后就去与他管辖的马帮队伍汇合,浩浩荡荡穿过丽江古城那狭窄的街巷,经过拥挤的四方街的广场和店铺,翻过狮子山的山梁,迎着从金沙江峡谷里吹来的已经暖融融的春风,沿着一条条从玉龙雪山上流下来的清澈无比的溪流,走出开满了野蔷薇花的丽江。
一开始赵应仙并不想骑到他的坐骑“红比”那浑圆的背上,自己一步步走出丽江坝会使他觉得心里好受一些。“红比”很懂事地走在主人的后边,连响鼻都没打一个。那是赵应仙供职的“达记”商号配备给他的专用坐骑,它已经跟他在西藏走了很多趟。赵应仙在哪儿,“红比”就跟着在那儿。“红比”是一匹铁青色的骟马,温驯听话。“红”在藏语里就是铁青色的意思。人们往往用牲口的皮色来给它们取名字。
然而,此时此刻,就是懂事的“红比”也无法理解赵应仙的心情。这么一走,就意味着离开家乡和亲人大半年。细心而温情的赵应仙永远忘不了多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妻子时给他留下的遗憾。
赵应仙很早就离家到德钦投奔在那儿做生意的叔父,但叔父的生意很小,他就在著名的“达记”店铺里当了小伙计。当了几年学徒后,赵应仙已经成人,家人给他带信说已为他在丽江选定了结婚成家的伴侣,要他结束在德钦的学徒生涯,回丽江成家,支撑起一个家庭。赵应仙很快结清了在德钦的一切事项,匆匆赶回家乡。他甚至完全不知道家里为他娶了个什么样的妻子。在纳西族地区,年轻人的婚事完全由父母做主,自己是没有选择伴侣的权利的。赵应仙作为家里的独子,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只有相信自己的父母会为他安排下一门能使他满意的亲事。事情也果然如此,赵应仙结婚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然而,仅仅跟新婚燕尔的妻子在一起生活了大半年后,赵应仙又得踏上茶马古道去为一家人的生活而奔波。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待在家里过儿女情长的日子。一个男人总不能就守着老婆过一辈子。再说,那时茶马道上云南与西藏、印度之间的贸易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大家都希望在那条路上获得利润和收益,已担起一家人生活重担的赵应仙自然不能例外。赵应仙没想到的是,他第一次走茶马古道,一去就是两年。等他从西藏回来,这才知道妻子已为他生了个儿子,而且差点在难产中死。
在半个多世纪后,赵应仙提及可怜的妻子还觉得有些负疚和寒心。他简单的卧室里端正地挂着他已去世的老伴的黑白照片,他把它放大了装在镜框里。就是这位病弱瘦小的女人在赵应仙走草地做生意的时候,在丽江撑持着一个家庭,上要侍奉老人,下要抚养孩子。她还要主持着将家里自己无力耕种的十几亩土地出租给别人耕种,从而得到一些租粮,另外自己又在家里夜以继日地织布出售,换一点钱,同时还在家里做一点酒卖。这在当时的丽江,几乎是家家户户最普通的生存方式。当然,养猪养鸡更是一个家庭的必须,她甚至还像有些人家一样,在家里养起了骡子。在那时的丽江,一头骡子就是一笔相当大的财富。我想,大约只有像纳西族妇女这样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和富有爱心的女人,才能承受那样一种沉重而艰难的生活。
走西藏草地的赶马人倒不会过年时出门,但他们走的路却格外漫长而危险。是啊,路途是那么漫长险恶,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天晓得有什么在前头等着赶马人。家人从此开始长得难耐的担忧和等待,而留在丽江的家人也让上路的人放心不下。这是真正的天各一方。相互之间在大半年里不可能有任何的联系,也听不到一点音讯,只有没完没了的担心和思念。那响过茶马古道的铜铃声不知牵动着多少人的心。
告别丽江古城
赵立仙牵着“红比”走过长长的有点斜坡的小巷道。巷道虽然窄仄,却也是店铺毗连,一个个皮匠、成衣匠、鞋匠埋头在自己的店铺里忙碌着。赵应仙并不是太羡慕他们能够天天待在家里,呆在老婆、孩子身边。再说,除了会拉拉琴自得其乐一下,赵应仙并不会其他技能。他的祖上只传给他走西藏做生意这门糊口谋生的本事,他只有上他的路。
巷道尽头一个急拐弯后,就是丽江城里著名的大石桥,踏过平缓的桥面,很快就到了丽江城的中心四方街。在这片好几亩大的四方形广场周围,聚集了数十家商号和店铺。形形色色的货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又从这里流淌到四面八方。
据说,丽江古城的形成,尤其是形成它那独特的格局,就是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不像中原文化所产生的城市格局,如以权力机构为核心,并形成中轴线,然后严格按有关规矩和等级制度,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大小尊卑有序排列,左右对称。它也没有任何欧化的影子。
丽江纳西人都把丽江古城叫做“巩本知”,“巩本”在纳西语里是仓廪之地的意思,“知”就是“街子”,也就是集市。由此可知,像云南的许多城镇一样,丽江古城也是由道路驿站而逐渐形成的物资集散地,最终人烟辐辏,成为了远近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导致丽江成为城市的道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
从地理上看,丽江位于滇藏川的交接点上,“踞全滇之上游,通巴蜀之要塞”,“自内地入藏,必以丽江为正路”,所以,它历来是这一区域经济文化交流走廊的重要关口。历史上的滇藏川贸易,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等的交流都在这里汇集。丽江古城的形成,直接与马帮的活动有关。
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区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清嘉靖年间,丽江纳西族中的“藏客”崛起,开始大规模前往西藏经商。从那以后,丽江人自己和其他人就把那些赶着马帮前往藏区做生意的人们叫做“藏客”。像大研镇人李萌孙就将商号设在了拉萨,在拉萨坚守信誉,并资助清廷驻藏大臣,被藏族人尊称为“聪本余”(生意官、大老板之意)。此后,纳西商人到藏区经商者越来越多,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他们不仅遍布西藏各地,而且进入了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较大的商号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杨家的“永聚兴”等等,后来更发展到30多家。据一些资料统计,到抗日战争时期,丽江在滇藏印茶马道上做生意的大小商户竟有1200家之多。
与此同时,西藏及各地的商家也纷纷到丽江设店开号。大批西藏的马帮将丽江作为进入内地进行贸易的中转站,而各地的马帮也将丽江作为进入西藏、印度的中转站,像大理喜洲帮的“永昌祥”,保山、腾冲腾越帮的“洪盛祥”“茂恒”,鹤庆帮的“恒盛公”,中甸帮的“铸记”,都在丽江开设分号。浩浩荡荡的马帮的来往,必然对丽江古城的建筑格局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为商旅云集,才使得丽江坝子里原本是一些各自相对独立的村落逐渐联合成了一座城市。在过去,丽江城的街道大都叫什么什么村,如乌伯村、托村(现在的福慧路、民族广场一带)、积善村、双善村等等。现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叫村了,但当时一些村名沿袭到今天,就成了现在街巷的名称,如“积善巷”“现文巷”等等。
那时各地来丽江的马帮就习惯性地聚集在一个个已经连成一片的村里。像城北的双善村,就是藏族马帮最喜欢落脚的地方。而大理来的行商,一般就住在一个叫“建洛阁”的巷子里。纳西语里将大理称为“建洛”,“建洛阁”意即大理行商住的巷。
优雅而又较完好地保存了古风的丽江古城,至今仍然是许多游子心目中的理想境地。她之所以具有那种别的地方都已经缺乏的怀旧情调,大概跟已经消失的马帮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生存发展之路
渐渐地,亲切的古城和美丽的丽江坝消失在石板铺成的山路的尽头。家越来越远了。赵应仙的心头照样又冒出一股很难受的滋味。每次出门这种滋味总是压抑不住地会冒出来。要不是生活所迫,要不是为了生存,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亲人,去走上这条艰难的路呢?
由于地域的关系,世世代代居住在丽江坝的纳西人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进入西北方的藏区,用贸易,用交换,来扩展生存的空间,来提高生活的质量。在历史上,纳西人的生意大多往西北的藏区发展,那儿才是他们驰骋的天地,那儿才是他们如鱼得水的市场。用他们的老话来说,这叫“熟门熟路,找钱更易。”
自古以来,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生息地区,东北部居住有彝族,西北部毗邻藏族,南部与白族和汉族的势力范围相接,丽江就正好处于汉、藏、白、彝四大经济势力圈的交错地带,其间还杂有傈僳、普米等民族,为纳西族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贸条件。
分居各地的各民族从各自的需求出发,自然而然要作各地间农作物以及其它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易,尤其是生活在高原特殊地域里的半游牧半农耕的藏族特别需要与内地的交易活动,仅他们每日必需的茶叶一项,就完全靠内地输入。
然而,西藏的马帮来到丽江,就再不可能继续前行,自己到山下的内地去。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更适应不了山下那炎热的气候。他们只能走到丽江为止。而内地的商人也难以进入西藏,他们面临的正好也是藏族面临的问题:语言不通,生活习俗迥然两样,高原的寒冷缺雪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他们也只能走到丽江就打住。于是处于内地与藏族地区交界地带的丽江成了西藏与内地之间交易的中间地,成了这一带各民族中转交易的地点。
赵应仙的祖上很早就在这条茶马古道上走动了。他的祖上本姓杨,后来过继给赵家才改姓赵,于是赵应仙的爷爷赵怡就将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取作赵育杨和赵根杨,既不忘赵家的养育之恩,也不忘杨家的根。赵应仙的爷爷赵怡几乎在茶马古道上走了一辈子,这条路不仅使他在丽江古城里(现在的五一街)盖起了两院房子留给他的两个儿子,而且还置了十几亩田地给后人作衣食饭碗。从那以后,赵家两兄弟分住紧邻的两院,小儿子赵根杨,也就是赵应仙的父亲,由他在家坐镇,照看田地和家人,而大儿子赵育杨则继续在茶马古道上经营生意,继承了家里在德钦的店铺,并养了一些牦牛打酥油卖,将挣到的一点钱带回丽江老家养家糊口,使家人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那时,丽江的大部分人家都是这样安排一大家人的生活的。种地的种地,经商的经商,里外配合,构成了当时丽江纳西人的生活格局。在那一时代,丽江人不可能还有别的生活方式。
商号与马帮
赵应仙一行二三十匹骡马,四五个人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在狭窄的山路上,马帮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行进。赵应仙虽然名为这支马帮队伍的最高管事,拿马帮的行话来说,就是这支马帮的“锅头”,但这支马帮并不属于他本人所有,他也很少过问马帮本身的事务,他只是他所受雇的商号的代理人,负责将货物在滇藏茶马古道上运来运去。骡马和它们所驮运的货物,自有赶马人照料。马帮有着自己严格的规矩。在当时的云南,商号与马帮之间已形成了现代特征的商业关系。
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有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匹。在一些小范围区域之间,更有无数小马帮营建起蛛网般的运输线,将物资的运输交流几乎覆盖到每一个村寨。有的马帮在川滇黔桂藏作跨省运输,甚至常年往返于印度、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家,有的在省内外,国内外与火车、汽车进行货物接转运输。于是,马帮形成为有特定组织形式和营运管理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方法的专业化运输集团,类似于今天的运输公司。有人甚至将一些规模庞大的马帮称为“马帮托拉斯”。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
一队马帮一般来说由“锅头”、赶马人和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库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
马帮商团化还有一个特点,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有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有些马锅头在搞运输发了财以后,也将资金用于兼营工商业,形成了自产、自运、自销的经营方式,虽然规模无法与大商号相比,但与那些家大业大、专业化、商团化的马帮一起,对云南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早在清代,丽江纳西族李悦、杨永蠼、李鸿旭、杨恺(开)、王树桐、李继斋、赖耀彩、李鸿芬、和瑛、周景汤、杨子祥、李达三、杨崇兴等人的商号和马帮就已经形成规模,有的多达五六十万元之巨。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的大小商户计有一千二百多家,有的还将商号开设至下关、昆明、中甸、德钦、康定、成都、昌都、拉萨、缅甸、新加坡、尼泊尔、加尔名答、苏门答腊等地。
赵应仙就是受雇于李达三家的商号,负责为其管理“达记”的一支有二三十匹票马的小马帮,有时骡马数目也会增加到四五十,最多时会达到七八十,视货物运输的需求量而定。
马锅头与马脚子
抗战时在昆明念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先生见过云南的马帮。他在他的散文《跑警报》中这样写道:“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都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多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哗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这的确是对云南马帮的很好的写照,但显然,走西藏雪域的马帮没那么悠闲浪漫,而且,赶马人并不等于就是马锅头。
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身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了赶马的路。
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个马脚子最多照管十二匹骡马,这当然只有那少数极能干的赶马人才能做到,主要是奔子栏的“马脚子”才赶得起,他们最得力了。一般的赶马人一般就负责七八匹骡马。一个赶马人和他所照管的骡马及其货物就称为“一把”。这样几“把”几十“把”在一起就结成了马帮。
马脚子的工作非常辛苦。从丽江到拉萨,他们真真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每天都要起大早,路上要生火做饭,要上驮卸驮,要搭帐篷,晚上睡到半夜也还要爬起来看看骡马跑远了没有,是不是安好。骡马一上路,他们背上拴马索跟上就走。有时碰到特别危险的路段,还要赶马人将货物卸下一趟趟背过去,以免骡马和货物发生事故。
赶马人不仅吃苦耐劳、勤快能干,富于合作精神,他们的嘴巴一般都很厉害,因为天天在路上边走边练嘴,要不很难忍受漫长路途的艰苦。如果是途经村庄碰到姑娘媳妇什么的,他们更是放肆地说笑起来,姑娘们往往就躲开了,而泼辣的媳妇们则会报之以笑骂,而这只能使见过世面、脸皮很厚的赶马人开心地大笑。那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很大的乐趣。
其实村民和赶马人一样的寂寞。对茶马古道上的许多村庄和牧场来说,当时能见到个异乡人跟见到外星人差不多。马帮的到来无异于一次盛会。在藏区就流传这样动人的情歌:
听到走马的铃声,
心里又喜又惊,
慌乱中提了只奶桶,
大大方方走出帐篷。
父母问小猎犬为什么吠叫?
我说畜群走回村中。
父母问跟谁说话?
我说是百灵岛掠过天空。
赶马人就这样路走去,带着新奇,带着某种希望,带着鲜活的气息,搅动了不知多少年轻人的心房。
原文发表于2010年3月19日《云南政协报》5版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李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