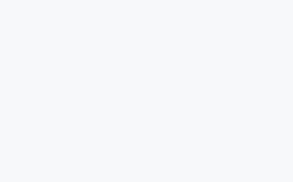深圳应该是产茶的。深圳东部华侨城的茶溪谷,满山满谷都是茶,是三洲田最吸引人的风景。
既然深圳现在能种茶,那以往的岁月大概也是种茶的,只不过房前屋后的三五株茶树,村里村外三五片茶林,尚不足以成为记忆里的风景,以至现在对于深圳历史上产不产茶,都印象模糊了。
史书记载,深圳曾产盐、鱼、茶、香、米、珠,出名的茶园却不可考。一方饮茶成习的水土,星星点点的些许茶树,不成规模的几爿茶园,谁会去特别留意呢?

但是深圳的近代历史,确乎与茶有脱不掉的干系。英国人学会了喝茶,并且上了瘾,拿着白花花的银子来买中国茶,眼看入不敷出,就使出了歪招:种植鸦片卖给中国人,以至于逆转了世界白银的流向。这当然不行,于是有了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进而爆发了“鸦片战争”,也有人说这是“茶叶战争”:茶叶贸易失衡导致的中英战争。
战争结果,香港割让给了英国。香港与深圳,原本都属于那时的新安县。深圳家门口土地,被完全陌生的西洋人占了,背后原因竟然跟中国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关,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不仅把英式红茶带到了香港,还变戏法似的把一整套西式生活方式和场景带到了香港。

深圳人算是最早看到这些“西洋镜”的中国人了。其时,香港、深圳往来自由,罗湖桥头,人头攒动,繁华的深圳墟甚至一度被称为“东方的蒙地卡罗”。即便是在深、港之间隔着铁丝网的那些年,深圳本地人也可持“耕作证”过到深圳河的对岸种田种菜。那时的深圳,一度是冒死赴港的人们日思夜想的地方。
如果说,是对深圳河对岸咖啡红茶的向往,促成了深圳的改革开放,那也并不为过。欧洲人的大航海、地理大发现,是始于对东方繁华的记忆与想象,那么,香港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都市繁华,为什么不能引发深圳人对美好生活的冲动与行动呢?
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广东人引进了香港的手袋加工厂,面向世界的中国决策人同意了香港招商局在蛇口的试验。深圳的财富之门轰然洞开。

1979年,深圳30多万人,GDP不足2亿元,人均GDP606元;2022年,深圳1700多万人,GDP超过了3万亿元,人均GDP18万多元。40多年间,深圳经济总量增长了15000倍,人均财富增长了300倍。这既是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也为深圳人的生活样式打开了万千可能。
深圳奔涌的市场财富,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投奔者。他们带来了五彩缤纷的故乡文化,也带来了五花八门的饮茶习惯。广府早茶、客家擂茶、潮汕工夫茶;江南绿茶、湖南黑茶、四川盖碗茶;福建铁观音、云南普洱茶、广西六堡茶,等等,等等,争妍斗艳。
深圳是中国第二个聚居所有56个民族的城市,深圳也聚集了最为花样繁多的饮茶方式。一座深圳城,堪称中国茶生活博览馆。

五湖四海的人们,当然首先是习惯成自然地按照老家的方式饮茶,接下来就会发现别人的饮茶方式与自己不同,在你来我往的陌生人的交际中,渐渐发现各自茶文化的差异,慢慢调整并养成新的饮茶习惯。
如此一来,深圳不仅有了茶事创新的财富实力,也还有了茶事创新的客观机缘。立足深圳,观察中国茶事,比较中国各地的茶文化,洞见城市茶事之未来,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大为方便。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深圳茶事之澜,映照的是深圳经济社会民生的潮流。早期劳动密集型的初加工业,吸引了来自天南地北的务工者,也带来了深圳茶文化的多样性。
市场经济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商务茶在深圳茶生活中的主流地位,不论是“工夫茶”还是“麻将茶”,都与商务交际和商务休闲有关;高科技的制造业,为茶器、茶具的迭代更新提供了技术可能;巨量的进出口贸易带来的财富盈余,为精品茶、高端茶的消费打开了空间,茶作为奢侈品、投资产品,融入到深圳城市生活的中流。

来闯深圳的人,往往以草根出身和不安分的性格而著称,他们的内心,既坚韧如铁,又柔情似水,禅茶之道,恰能给予宗教般无所不包又细致入微的关怀;与全世界做生意的深圳人,展示给世界的是什么样的外在姿态和内心修为?喝茶的样子,可以是最好看的。喝茶的功夫,也是最值得修炼的。全世界都悦纳的东西,真的不多,茶是其中之一。
19世纪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曾将西方文明的启蒙归功于欧洲从烂醉如泥的酒鬼国度成功转型为喝咖啡的理性社会:“文艺复兴抒发的新思潮,部分归因于一件足以养成新生活习惯,甚至改变民众气质的大事件,那就是咖啡的出现。”东方文化尚酒,也尚茶。闹里饮酒,静处喝茶。
深圳人仰赖酒精的草创时代已近尾声,茶,作为清醒之饮,是深圳步入成熟商业社会的东方之选。

著名作家林清玄先生曾说过:“喝茶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茶’字拆开,人在草木间,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尚能合一,东西方为何不能合一?和合世界,从茶开始。
当然,深派茶道,也才刚刚开始。《深圳茶事》《城市茶事》也才开始上道,我们的茶事之旅,是去求道,求取茶道真经,远没有布道的资格。






本文源自:晓德书号,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